记忆十八
高一八班
作者: 黄敏88届澳大利亚•珀斯
一九八五年夏天,我碰上了一桩好事——省城重点高中头一回从我们五区八县招收保送生,不用中考就能直接去读。办了好几道手续后,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。进了学校才知道,所有像这样从县里保送上来的学生,都给分到了高一七班和高一八班。我也就荣幸地成为了高一八班的一员。
全班四十余人,如今数字早已模糊。其中男生占了大头,女生仅有八个,屈指可数,像撒在旱地里的几粒豆子。那会儿男女界限分明得很,谁要是多看异性几眼,立马就有促狭鬼起哄:某某和某某有情况!或许因七班八班都来自县城郊野,彼此间倒颇为熟络。不少人原本就同校甚至同班,如今竟在省城又续上了同窗的缘分。女生既如此稀罕,无形中便成了班中珍物。其中一位,与我同姓,来自一个县,是位文理通吃的学霸。我那时正值青春期,管不住嘴,脸庞圆鼓鼓的,她个子高些。一次语文课上,老师竟指着我们俩,半开玩笑地起了绰号:这是‘大胖’,那是‘小胖’!后来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,还有人笑着问起:“咦,不是‘大胖’‘小胖’吗?如今看着都不胖了啊?”时光这把“杀猪刀”,倒把当年那点青涩的胖意给细细剔除了。席间笑谈正酣时,我忽然想起另一位女生,个子娇小,总是安安静静的。便随口问起她的近况。热闹的场面忽地静了静,有人低声告诉我:“她……已经不在了。听说是生病……” 后面的话被叹息掩去了。我一时怔住,眼前浮现出她总是微微低着头、抿着嘴笑的腼腆模样。那个曾经和我们一同挤在狭小宿舍间,为同一个大学梦埋头苦读的鲜活生命,竟已悄然隐没在岁月的河流里,无声无息......

图1:作者(中)
考大学,似乎是那个年代我们这群少年人唯一能想象的天梯。至于“素质”二字,当时还在远处沉睡,未曾醒转。可班中确是藏龙卧虎:但凡能保送至此的,岂有泛泛之辈?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竞赛的奖状,从县级市级甚至到国家级,如同春树繁花,纷纷开在同学身上。所谓山外有山,原来并非虚言。那山就真真切切矗立在我课桌咫尺之外,让人不得不屏息仰望。
我的同桌就是一位来自连江的姑娘,才华横溢,初中时就拿过全国作文竞赛的奖。每每我在物理题海里焦头烂额,连门道都摸不着边的时候,眼角的余光瞥见她,人家早已笔走龙蛇,干净利落地写完,起身交卷去了。那份从容和聪慧,真真只有望其项背的份儿。
平心而论,有些同窗之优异,着实令我瞠目。譬如那位Y君,他几乎日日上课都埋头于小说之中,那副神气,似乎只当讲台是空物。然而每次考试,他的分数却总如星辰般高悬于众人之上,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时风靡的读物,金庸的江湖、琼瑶的庭院,还有一位叫“岑凯伦”编织的情网,全是他书桌的座上宾。他常将那小说套在课本的封皮里,目不旁视地读;老师巡视在四十多张课桌之间,竟也难觉察——大约是少年人那份全神贯注于隐秘乐趣的劲头,本身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
受Y君的“启发”,加之一位要好的同学推荐,我得了份“美差”——在学校图书馆帮忙整理书籍,搁现在叫“志愿者”。那间弥漫着旧纸与油墨香的小屋,成了我三点一线生活里意外透气的天窗。趁着整理书架的空当,我囫囵吞枣地读了许多本“闲书”:霍达笔下北京回民家族的悲欢离合(《穆斯林的葬礼》),路遥描摹的黄土高原青年抉择(《人生》),铁凝那本像面镜子似的、照出我们这群高中生心事的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(当时大家更爱叫它《红衣少女》)——书里那个敢穿红衬衫、敢说真话的女学生安然,简直成了我们心底偷偷向往却又不敢做的另一个自己。我甚至还斗胆翻过几本讲“人心”的厚书——弗洛伊德《梦的解析》里光怪陆离的潜意识,马斯洛《动机与人格》中“自我实现”的阶梯,阿德勒探讨自卑与超越的挣扎(《自卑与超越》),还有皮亚杰的《儿童心理学》,那些拗口的术语像另一个世界的密码。对于当时那个来自小县城、内心交织着自卑、倔强与一丝叛逆的少女来说,这些书籍,尤其是那些厚重的小说和试图解读人心的文字,像一把生锈却有力的钥匙,硬生生捅开了锁死的心门。当别人在题海中鏖战正酣时,我缩在图书馆角落啃小说、翻“闲书”。在那资讯贫瘠如荒漠的年月,这些纸张粗糙的书籍,如同不期而遇的向导,引着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一个远比课本和试卷辽阔的世界: 窗外吹来的风,混杂着玉器世家的叹息、陕北高原的尘土、少女安然身上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掀起的微澜,还有心理学试图解剖人性的笨拙刀锋——它们冲淡了试卷的油墨味,让我这井底之蛙般的少女,第一次懵懂地探出头,窥见了人世间原来有如此参差多态、深不见底的风景,也让我在那个只论分数高低的单一世界里,找到了一处暂时安放惶惑与躁动的角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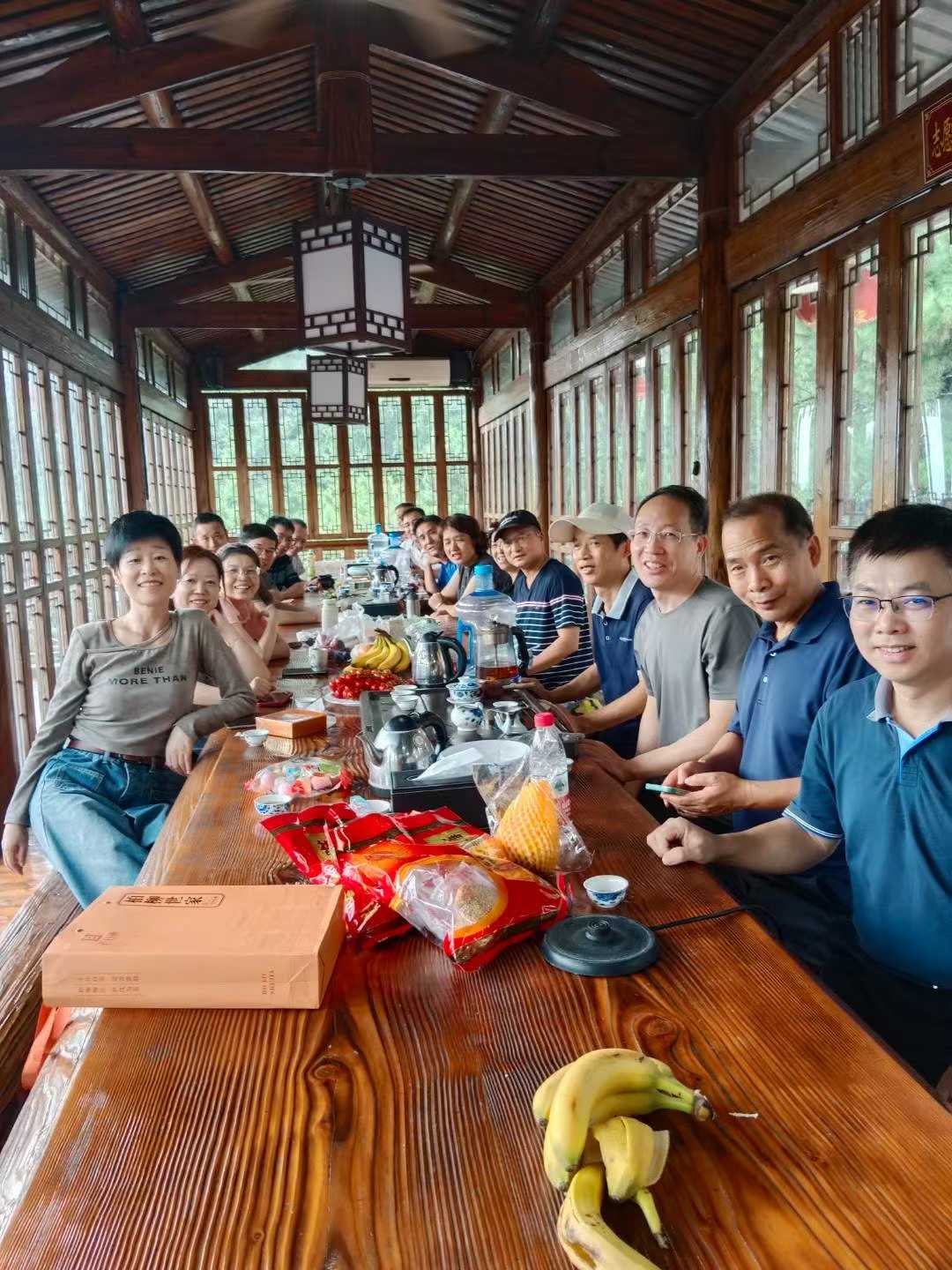
后来我旅居异国,或许正是受这位Y老兄无形点化,竟拿金庸的武侠世界作了教孩子中文的课本。自然,那些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,原本也是我心底的旧欢。如今每每听到当年《射雕英雄传》主题曲的调子,那旋律便如一把钥匙,猛地旋开了记忆的铁锁, 让我回想起曾经青葱的岁月。人们常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歌谣,其实歌声里藏着的,是整个时代沉甸甸的私语。
如今回头想想,高一八班的日子,三点一线,试卷堆得比人还高。那些只知埋头苦读的岁月,竟成了往后人生里再难觅得的纯粹时光。而那份苦里头,又藏着金子般的亮光。亮光里有“大胖”“小胖”被叫起绰号时涨红的脸,有那位娇小女生低头写字时露出的安静发旋,有同桌才女笔下沙沙作响、飞快解题的笔尖,有Y君课本底下金庸江湖的刀光剑影,还有图书馆旧书架上,霍达写的玉、路遥写的黄土坡、弗洛伊德画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……它们像压箱底的旧照片,边角都磨毛了,可一翻出来,当年那股子混合着油墨、粉笔灰和少女汗味的空气,仿佛又扑面而来。当年的日子是清汤寡水的,可我们这群半大孩子,愣是在这清汤里,凭着各自心里那点倔强和好奇,捞出了点不一样的滋味。那些课本缝隙里偷运的闲书,图书馆角落里啃下的文字,连同刷不完的题、考不完的试,还有那些再也无法重聚的笑脸,一块儿搅和着,酿成了只属于高一八班的那一年——感恩!

(Min 2025年8月9日于珀斯)
- Log in to post comments